《刘再复八十年代学术环境》:关于免费刘再复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刘再复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上世纪八十年代您曾担任过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经历了文化界在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历史性节点,很多人说您是当时参和文化界改革的一个代表人物.
刘再复:有人说我是文化界“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这是一个政治概念.用这种概念描述我,并不准确.我始终是个文学中人,文化中人.但我应当承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充满参和社会改革的热情,首先是清除“ ”政治毒素的热情,这种参和,在当年的历史语境下,又确实带有政治性.加上我当时已是 党员(1978年入党,1979年转正),在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又兼任党组书记,所以有人说我是“党内改革派”,也并非恶意.
那时和所谓“保守派”(现在我不再使用这类政治语汇)的分歧主要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问题.我讲“文学主体性”,也是为了争取作家的“艺术主体”权利,即在创作中拥有充分个性自由的权利.每个作家的主体首先可区分为现实主体和艺术主体.作为现实主体,你是党员,当然会讲党性、纪律性;但作为艺术主体,你则有权利超越现实主体的限定,赢得现实主体所没有的自由,诸如见证人性、展示个性的自由.当时我在政治上从来没有怀疑过经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是保守派也可以,但在文化上我却不赞成保守,即不赞成交心运动、斗私批修运动等,不赞成对作家心灵进行种种干预和限制,争取的也是心灵自由.当时我想摆脱阶级斗争时代的阴影,针对的是“理”不是“人”,所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人物.在我的心目中,“对方”好像只有不断批判我的《红旗》杂志.后来《红旗》的名字被改为《求是》,我感到特别高兴.
您在担任社科院文学所长时,为俞平伯先生庆祝生日,其实也就是为他平反.这在当时遇到什么阻力么?
刘再复: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我提出“学术自由、学术尊严、学术美德”的办所方针,提出这一方针,不是空话,所以我便着手筹备庆祝俞平伯先生八十五诞辰的纪念活动,借此给俞平伯先生“平反”,也给学术自由、学术尊严作证.我的这一“行为语言”,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社会科学院内没有阻力,胡绳院长过问一下,实际也支持. 任何部门都没有干预此事.俞平伯先生的纪念会于1986年1月召开,和会者四五百人,盛况空前.“平反”能得以顺利进行,说明当时的人文环境、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文化界这样宽松的人文环境之后也遭遇过一些反复吧?
刘再复:是的,可惜好景不长,“平反”会后不久,很快就发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所倡导的“学术自由”,也被视为自由化嫌疑.运动之中,我虽然未被点名为“精神污染”,但蒙受了精神压力.我的胆魄不够,一旦有精神压力,该说的话就说不下去.例如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胡风“主观论”,甚至被视为涉及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把我从学术话语中拉到政治话语中,而“主体性”的真问题反而无法深化下去了.文学主体性的真问题还得进入两个层面,一个是“主体间性”(也可称“主体际性”)问题;另一个是内部主体间性问题,即自我内部的本我、自我、超我关系问题以及主语三人称(你、我、他)的语际关系问题.直到今天,我还有只讲主体性、未讲主体间性的负疚感,因为讲主体性只强调了张扬自我,讲主体间性才能平衡自我和他者的权利界限,才能在理论上说明“自由”和“限定”的关系,才能避免张扬自我时变成膨胀自我而犯精神浮肿病.现代中国人普遍犯有精神浮肿病,我可能也有一份责任.
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先生曾严厉批评您“建立了一套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将学术之争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这种论争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刘再复:姚先生开始对我也是尊重的,他曾委托一位朋友,交给我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要求我支持他在武汉即将成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可是我没有答应.因为北京已有一个当代文学研究会,而且已挂靠在文学研究所了,如果再成立一个研究会,就会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山寨”.我的谢绝可能让姚先生生气了.之后他在《红旗》杂志连发几篇文章“炮轰”我,认定我“反马克思主义”,这才逼得我接受《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先生的采访,谈论了“姚雪垠现象”.当时我还没有学会“妥协”,便“以牙还牙”,挖苦姚先生的《李自成》顺从政治意识形态,把李白成、高夫人写成“高大全”英雄,违背性格真实和历史真实,导致《李白成》一卷不如一卷.从而惹得姚老非常生气,以致声言要到法院告我.
回顾那场争端,觉得双方都没有“进人问题”的冷静,过多情绪化语言.姚先生用“重炮”,固然过激,我回以“机枪”,也太不留情.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如果再面对这种争论,我当会理性地阐明“真问题”,不会再计较他者的“上纲上线”,出国之后,我已告别了“文化大革命”的心理阴影和语言方式.
很多人说您这一代人是鲁迅精神养育的,而海外的夏志清等学人更倾向张爱玲.后来您一直生活在海外,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再复:如果说我的同一代人甚至前后的两三代人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这是事实,但就个体生命而言,说我是“鲁迅养育”的,则过于本质化即过于简单化.在最重要的青少年时代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高尔基、契诃夫对我的影响超过鲁迅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我并不是被鲁迅所养育,而是被外国文学作品所养育.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的读书范围基本上就是马克思、 、鲁迅的书,说这十年被马克思和鲁迅所养育,倒是真的.
和鲁迅相比,张爱玲的影响只限于文学层面,并未广泛地进入社会层面.只有在台湾和香港,张爱玲的影响才进入社会层面.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确实写得很好,但是到了《秧歌》、《赤地之恋》,便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了.就文学创作整体的丰富性而言,她远不如鲁迅,更不用说思想深度了.夏志清先生重新开掘张爱玲,很有功劳,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犀利坦率,没有“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也受到冷战时期两极对峙思维方式的影响,政治倾向太强,所以抑鲁扬张,未能正视鲁迅的博大和深邃.
您在前几年和李泽厚先生一起合著了《告别革命》一书,这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刘再复:我们提出“告别革命”只是善意地期待,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使用暴力方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中发现历史上的大革命即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我和李泽厚认为,面对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永远都有)只有两种基本选择,一种是用“阶级调和”即改良、协商、妥协的
刘再复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刘再复八十年代学术环境为大学硕士与本科刘再复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刘再复弟刘贤贤方面论文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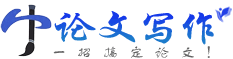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