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的文化史》:关于免费维多利亚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维多利亚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访问整理者按 伯纳德·莱特曼,加拿大约克大学人文科学系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2004-2014年担任爱西斯(Isis)杂志主编.主要从事科学的文化史研究,特别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宗教与文化的研究.2010年8月,莱特曼教授在北京大学参加“传播中的达尔文”国际研讨会期间接受了采访.访谈涉及的问题有科学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对科学普及的历史研究、反思“公众理解科学”、科学职业化的解释模型、科学家传记辞典的编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科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本文的英文版见《剑桥研究杂志》第5卷第4期,中文版文字略有改动.
柯遵科(以下简称柯):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进入科学史研究领域的?
莱特曼:我在约克大学读本科时,参加过一门非常好的关于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科学和宗教的历史课程.它由悉尼·艾森教授(Sydney Eisen)讲授,当时我就被吸引住了.因为这门课,我决定去攻读研究生,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和宗教.但是在当时,我认为自己做的是思想史,或者说观念史.我并不觉做到自己是在做科学史,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史还完全不同于现在这个样子.科学史是由科学家或者受过科学训练的学者来做的,它只关心科学观念,而不关心科学的文化和社会语境.我在波士顿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 in Boston)读观念史项目的博士,从我去之后的那一年起,这个项目再没有招收过新生.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不可知论的起源,讨论科学和宗教的观念.1979年我获得博士学位时,思想史专业没有工作职位,因为社会史在那一时期正在兴起.所有的职位都是社会史方面的,思想史方面根本就没有.所以我做过一系列短期的合同聘用的工作,虽然它们是全职的,但是只有有限的聘期.我是个吉普赛学者,换了很多的教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一天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我将找不到一个终身教职.于是在1985年前后,我开始更多地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开始去参加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的会议.我发现美国历史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过于庞大,它强调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这个协会太大了,以至于我碰不到同行.所以,我开始去参加规模较小的科学史学会的会议,我发现自己和科学史研究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当时这个领域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科学史研究已经开始走向认真地考虑科学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所以科学史研究者们也更关注我所做的工作了.但是,也还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完全被认可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我的第一本书《不可知论的起源》于1987年出版.它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修改.爱西斯(Isi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本书的书评,是我的朋友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写的.摩尔在书评中称我是一名思想史研究者,他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我的工作对于科学史研究者的重要性.我作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的身份,并不是马上就稳固地建立起来的.
柯:在您主编的《语境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一书中,您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您所做的不再是思想史,而是文化史,关注的是科学普及.那么,您为什么决定去研究科学普及者?
莱特曼: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研究不可知论者,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精英科学家.《不可知论的起源》一书重点考察了赫胥黎、斯宾塞、丁铎尔、克利福德和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斯蒂芬是里面唯一的非科学家.我对这个群体进行了10年多的研究.当我开始思考我的下一个大的计划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决定要转向某个全新的东西.事实上,当时是詹姆斯·摩尔邀请我为他主编的《历史、人性和进化》一书撰写一章,这帮助我构想出了我的新计划.在那本书中收入了摩尔的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讨论了达尔文的女儿安妮之死和这件事如何动摇了达尔文的信仰.这部文集是为了纪念约翰·格林(John Green)而编撰的.我做到想自己打算为这本书做点什么.在《不可知论的起源》一书中,有少量的篇幅,我讨论了19世纪80年代斯宾塞的一些追随者,他们是一群早期的世俗主义者.这些鲜为人知的人物传播了进化论和不可知论.于是我给摩尔主编的文集写了一个和他们相关的章节,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考虑将科学普及作为一个有可能写成一本书的计划.我意识到,既然在19世纪80年代有普及进化论的人,那么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也必定有其他的非科学家从事科学普及,而且不仅仅是普及进化论.我开始想弄清楚这些人是谁.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进行这个研究,用去了超过15年的时间,才出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不过,我就这个主题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为《语境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一书撰写的一个章节.
柯:您觉做到“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对科学史研究有影响吗?
莱特曼:公众理解科学实际上是为了让人们理解科学,看到科学的价值,并最终支持科学.它可能成为没有批判性的,因为它倾向于为科学歌功颂德.因此科学史研究者对它进行了反击.我试图表明,即使理解科学的过程也有一段历史,它远远要比仅仅由某个科学家声称科学是什么,然后公众被动地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复杂做到多.我现在对科学普及的历史研究,就是要试图表明公众理解科学比它的支持者所通常以为的要复杂做到多.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传播中的达尔文”国际研讨会,有一位发言者讨论了进化论在从达尔文传播到中国民众的过程中科学信息是如何丢失的.这是一种陈旧的科学传播模型.精英科学家掌握真理,他们把它写进书中,一位科学普及者随之出现,对它进行总结和简化,然而不知道怎么就搞错了,接着读者可能把它弄做到更错.在这个模型中,科普的目标是通过科学普及者向公众百分之百地提供《物种起源》一书中的信息.这里假设了一条笔直的传播线路:从科学家到普及者,再到读者.我在科学普及方面所做的历史研究试图表明,科学普及者甚至并不试图将《物种起源》一书的内容百分之百地告诉他们的读者.实际发生的情况更像是一种翻译过程.科学普及者将科学翻译成他们的读者可以理解的话语,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将某种可能并没有被包含在《物种起源》一书中的,关于科学的更大的意义的意识加入科学观念之中.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明确拒绝了详细讨论他的工作对于宗教和对于理解人类本性所具有的重大含义.但是普及者意识到读者想知道那些含义是什么.所以当他们普及进化论时,他们的首要目的是告诉读者,达尔文著作中的科学理论对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普及者对读者说我们将帮助你理解科学,但是我们也希望帮助你理解,关于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人类的未来,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他们并没有百分之百地传播《物种起源》中的科学,因为其本身并不是关键所在.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的模型,它假定知识是从精英科学家扩散到被动的读者那里去.我认为这种扩散的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当时成立了一个致力于传播知识的组织,名为“传播有用知识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这个学会由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发起成立.布鲁厄姆是一名辉格党人,他认为知识传播是进步的关键.他相信存在这样一个读者群,这些人希望从自己买做到起的书籍读到有关科学的内容.他想对抗那些试图将科学变成唯物主义的激进分子出版的非法书籍所造成的影响.传播有用知识学会出版的书籍通过自然神学将科学放进一个宗教的框架里.然而,布鲁厄姆的模型正是那种扩散模型,科学普及者将总结当前讨论的科学知识,随后读者将会被动地全盘接受.所以,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的模型是相当陈旧的.它并没有提供一个适当的模型来让我们对科学普及进行历史研究.
维多利亚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的文化史为关于本文可作为维多利亚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维多利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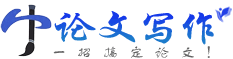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