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冷暖,百姓尊严》:这篇百姓尊严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这里我想谈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市井小说.这是当时比较松散的一个类型,一般涉及汪曾祺、陆文夫、刘心武等写城市下层平民的一类小说,但比如王安忆早期写弄堂和小杂院的作品,似也可以归入.我想从题材来讲,“下层平民”是要强调的,这使它区别于都市小说:如果说都市故事发生在咖啡馆酒吧,主人公是丽人绅士,那么市井故事则在弄堂街市,写的也是普通劳动者.但我下面想讨论的不仅仅是代表性或反映现实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如何写普通劳动者和他们的生活,也就是“审美形式”的问题.实际上现实主义虽在知识论上声称要反映现实,它在美学上却总是在赋予现实以某种审美形式,比如19世纪现实主义就赋予了新兴资产阶级生活以英雄史诗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初市井小说才引起我的注意,这些市井小说赋予了市井生活怎样的美学形式呢?
一
就市井小说的总体美学风格,汪曾祺在1988年出版的《市井小说选》的序言里有一个精当的说明:
“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平凡的人.“市井小民”嘛,都是“芸芸众生”(《<市井小说选>序》).
这里不仅涉及内容,更是提出了“反史诗”的琐碎的市井美学形式,这很关键.亚里士多德提出史诗之所以和散碎的历史事件不同,是因为它的意义被统一在了英雄行动(叙事)之中.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卢卡奇后来在《小说理论》里把小说看作在散文世界里重写史诗的美学努力:现代生活是琐碎的,但小说仍在美学层面上追求总体性意义.卢卡奇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洞察无疑是深刻的,但他对史诗和英雄的强调也带来问题的另一面,即非英雄的琐碎生活是否就丧失了美学资格?这在亚利克斯·沃洛克(AlexWoloch)看来是叙事学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位论者在《一个和多个》一书里提出了次要角色的“异化”现象:19世纪小说在塑造资产阶级英雄个体的同时,也在叙事内部“压扁”了劳工等边缘角色,这些角色的内在性和生活世界在叙事组织里被剔除,他们没有性格,少言寡语,不过是英雄完成行动的工具性要素.比如在普鲁斯特笔下,一个洗衣的女仆就是洗衣的人,一个花匠就是铺花径的人,关于他们的描述都被放在句子末端,这在句法层面上就否定了下等人获取自己视点的可能(见Alex Woloch, The One vs. the Many).
在完全不同的新时期语境里,汪曾祺提出了类似的下等人视点问题,这涉及到在美学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也有角色异化的问题.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初赵树理就提出过类似问题.他当时编辑《说说唱唱》,提出“用人民大众的眼光来写各种人的生活和新的变化”.这里“人民大众的眼光”不是左翼精英知识分子的眼光,也不是革命群众升华了的眼光,而是在评书、曲词这些民间文艺里提炼出来的市井普通人的眼光——赵树理当然考虑到反封建、“提高”等问题,但他争论的是民间文艺所表达的下层市井的“较低的”视点,寻常的市井故事,平民朴素的*生活有没有在美学上发展成人民文艺的可能?新政策下的《说说唱唱》很受读者欢迎,但这种对主流的挑战遭到左翼精英主义和官方话语的联合狙击,很快就失败了(见张均:《赵树理与<说说唱唱>杂志的始终》).汪曾祺在五十年代初做编辑时是赵树理的助手,在《说说唱唱》经历了杂志被批判、调整、解散的整个过程,他虽对这场争论没做评论,但晚年对赵有温馨的回忆.实际上在五六年他就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看不起大众文化、不理解民间情感的错误倾向(汪曾祺:《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还提出民间文艺是劳动者文艺,是“刚健、清新”的文艺.甚至在*强调英雄升华的“三突出”原则下,在汪曾祺参与创作的阿庆嫂身上,是否依然保留着寻常的市井眼光(如“人一走,茶就凉”)呢?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新时期文艺政策放松,汪曾祺避开抽象的工农兵去写下层的工匠挑夫,在上面这个脉络里看是回到赵树理的平民立场.不过在新时期反英雄史诗,汪曾祺直接针对的是当时改革、伤痕、知青文学里的(悲剧)英雄主义,这一点汪在《卖蚯蚓的人》一文里说得很明确.汪曾祺宣称他在城市贫民——卖蚯蚓的人——身上看到了审美意义,同时嘲讽那些自诩“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在后者看来,下层贫民只是社会无意义的填充物.如此刺耳的精英主义言论不可能出现在“十七年”和*时期,这和八十年代新启蒙话语有关;在叙事层面这时下层的次要角色的异化在文学里也频频出现了,比如《班主任》里的宋宝琦,《爬满青藤的小屋》里的王木通等.在这样一个话语环境里,市井文学整体上替小民视角辩护,在美学上严肃回答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普通人琐碎生活如何获得审美意义?这是一个大问题,下面只简单提提陆文夫等的反讽叙事和汪曾祺等的风俗描写.
二
陆文夫在1956年写《小巷深处》,写改造后的*在新生活里的矛盾,已透露出他向下层探求的努力.他被打成*后下放工厂农村,这种向下的经历反过来在创作上给他带来了帮助.他在新时期作为*分子写作,情感上却更认同市井,这就使他在处理知识分子和下层贫民视角上有了“反讽”的张力.
这里的反讽我用的是亨利·詹姆斯的意思.詹姆斯发现,在写作中很难避免将次要人物扁平化,因为一旦次要人物的内在视点膨胀,就会和主导视点冲突.我们可试着假设如刘心武按照苏童的方式在《班主任》里发展宋宝琦这个市井少年的视点,那么启蒙知识分子张老师就会显得可笑,小说也就成了反讽.但詹姆斯的保守性阻止了他去进一步阐发视角冲突可能带出的不同阶层间的文化与生活世界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却在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等作品里获得了复杂的表达,作者有意让本该被压扁的市井小民视点膨胀起来,从而腐蚀、瓦解了“我”的启蒙视点.
在《小贩世家》里,“我”和小贩朱源达曾是好友,但自从“我”成为革命干部后就成了朱的启蒙者,决心要改造“朱”和他的生活.这一种面向他者世界的征服性叙事本该写成经典的“成长”故事,比如在《绿化树》或《北方的河》中的叙事,但在这个作品里“我”虽在政治经济上都比朱优越,具有抽象话语能力,在叙事上也控制着视点,却始终是一个孱弱的行动者:“我”被朱阴暗潮湿的生活世界所震慑,后者侵入并颠覆了“我”的叙事控制,启蒙也因之失败.相比于“我”的抽象理性能力,朱的优势在于与“物”的亲近,一方面是他贩卖的馄饨、鲜鱼活虾、菱角等物的世界带来的色彩气味光泽,这些描写性场面总是无声无息地渗入到“我”的抽象理念之中,显示出“物质”对“精神”的激烈反抗,而这一美学路径开启了后来新时期文学中的世俗化趋向.第二方面的力量则来自对朱的市井生存的局促性的认识,他深陷在生计窘迫之中,他的辛劳和狡诈因此是迫切具体、不容否定的.承认市井局促意味着对革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放松,陆实际上是将*评判放低到粗糙的庸常物质层面上,他的市井绝不理想,很多时候很冷峻(比如《井》《还债》),但他对底层人在实际生存中的挣扎有了更多体谅同情——在更广阔的寓意上谈,市井贫民的泥泞就成了革命理想或启蒙理性的解毒剂,这些抽象所不能到达的生活弄脏了美丽的宏图设计,琐碎的描写因而构成了宏大叙事的反讽性力量.
百姓尊严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寻常冷暖,百姓尊严为适合不知如何写百姓尊严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百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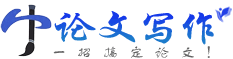

 原创
原创